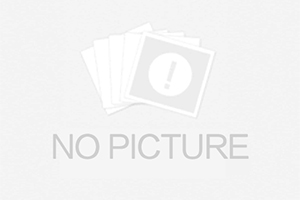两年前,我来到美国哈克伦。我打算找份工作,挣点儿生活费,可两周来什么活儿也找不到。那天晚上我回家后,心情沮丧地把自己抛到小床上。这时我的目光落在放在房间角落的古琴上,想起白天在哈克伦广场看见的那个卖艺的吉他手,一个念头忽然闪过脑际。
第二天一早,我便去市政府申请了街头表演的“营业执照”。就这样我开始了街头表演,不厌其烦地向围观者解说和演奏中国古琴。经过一周街头卖艺后,我总算开始拥有一些观众和收入了。一天中午,一个衣着邋遢的老头儿走来笑眯眯递给我一个大信封,神秘地眨眨眼:“这是给你的。”我打开一看,是我弹琴的照片,被印在几张白纸上。“怎么样,不错吧?”他得意地说,“我特地每张多印了几份,你可以用来送朋友。”
电子时代了,这种黑白打印机印出的图片对我没有多大吸引力,但我还是礼貌地谢了他。我又认真打量了他一眼,他身材高大,满脸皱纹和老年斑,大约有70多岁,发黄的白汗衫被凸出的肚子撑得鼓鼓的,胸前挂着一个银灰色的数码相机,与穿着极不相称。
“我是艾瑞克。你弹的曲子非常美妙,所以给你拍照,当做送你的礼物。”我口里敷衍着,低下头整理戴在手指上用来拨弦的弹片。可他似乎还没有想走的意思,又向我要电子邮件地址。我想快点打发他走,就写在一张小纸条上递给他,然后把这件事抛到脑后了。
两天后我上网查邮件,意外地收到艾瑞克的电子邮件。他说他无意干预我的生活,但他有一幢4个卧室的小房子,只住着他和一条狗。他说:“中国姑娘,你愿意来和我同居吗?”的确,我正想找一处条件稍好并且更安全的住房。然而,素不相识便让我无偿去当房客,难免会让人产生不好的联想,在中国遇到这样的人,我一定会问他为什么要给我提供免费住处?究竟有什么企图?但这是在美国,我不知如何是好,跟几个新结识的中国朋友说了这事,大家都认为不去为妥,甚至还有人好心提出要帮我找警署查一查他有没有“案底”。一周很快过去,艾瑞克又来找我了,说他天天都在等我的回音呢。还兴奋地说,如果我同意,他就要开始粉刷屋子了,见我犹豫不决,他建议我去他家看看再说。我答应了。周一我早早收工,跟艾瑞克通过电话,便依照他所指的路线骑车去他家。
骑了一段路,终于看到一幢掩映在浓密灌木后的浅蓝色小屋,正是他家的门牌号。我停好自行车,摁响了门铃,虽然见过艾瑞克几次,却谈不上熟悉,加上朋友们众口不一的评论,我突然有些紧张,不知这扇门后等待自己的将会是什么。艾瑞克很快出现在门口,跟他一起欢迎我的还有一条矫健的棕色猎犬。他幽默地说:“我和强恩欢迎你。”我被他的风趣逗笑了,很快放松下来。小屋不大,我跟在他身后,走过挂着手工壁毯和油画的狭窄过道,来到兼做厨房和客厅的正屋。可以说,这是我见过的最凌乱的屋子了。桌上各种书籍、卡片和瓶瓶罐罐堆得像小山一样,灶台上摆满了器皿、碗碟,满是面包屑;墙上、壁炉台上琳琅满目装饰着风格各异的工艺品,却大多积着尘土。
艾瑞克有点窘,歉意地说:“我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来电话……”我理解地一笑,靠窗坐下。窗边有一盆吊兰,盛在一个别致的白线网里,枝枝丫丫蔓延了小半个窗。
艾瑞克又带我参观书房和楼上几间同样凌乱的小卧室。书房里那套装备齐全的计算机、打印机和扫描仪,又让我暗暗惊讶。他指着记事板上贴着的一张合影说,他刚从小区夜校的计算机班结业,照片上的人都是他班上的同学。
我记不清那天我们还聊了些什么,只记得最后我同意了。艾瑞克高兴得跳了起来,握着我的手说:“你真的愿意和我同住了吗?天啊,感谢上帝!感谢你!”我还没来得及谢他,他却一个劲地谢我,我感到很迷惑。最后他接受了我每月支付水电费的要求,我才有些心安。
在小屋醒来的第一个清晨,我拥在被子里,充满喜悦地欣赏着我的新居。曾经凌乱的屋子被艾瑞克收拾一新,墙面也被粉刷成赏心悦目的浅绿。看看昨夜被我放在门后的木楔原封不动地留在原地,我有点儿不好意思地笑了。这两个木楔是一位中国同学专门为我做的,他让我睡觉前放置门后,万一有“情况”,门被推动,便会顶住木楔,使上面的长钉斜钉入地板,并且会越推越牢。当然这两个木楔此后一次也没派上过用场,但当时犹如一道护身符,让我心里觉得踏实。
这时我隐约听见屋顶传来细碎的响动。我好奇地下床拉开窗帘,晨曦中,只见艾瑞克手提一只桶,一把一把朝地上撒着什么。我正不解,又听得“呼啦”一阵响,一大片鸽子从天而降,齐刷刷落到艾瑞克撒过谷物的地上啄食。
原来,多年前的冬天艾瑞克捡到一只受伤的鸽子,喂养了几天它复原后飞离,却又带来两个伙伴,两个伙伴又带来更多的伙伴,渐渐竟成了一支颇具规模的鸽群。经济并不宽裕的艾瑞克每周都得去商店买来一大袋鸟食,他常唠叨说不能再喂下去了,可仍旧一袋一袋往家里买,还是一天不误地喂鸽子。为了生计,艾瑞克又操起退休前的旧业,给生病的小区居民做穴位按摩。
每天放学后我疲惫地回到家中,艾瑞克会拿来各种怪异的盘子,盘子里装着更加稀奇古怪的食物。花朵、树叶、云彩都是他用面包做成的,和他共进晚餐简直就像小时候玩积木一样。有一次,他用三明治和蔬菜摆成一栋漂亮的别墅,他说:“放一栋别墅在胃里,你这辈子就不必为住房发愁了。”我笑弯了腰,居然很轻松地吃完了这栋“别墅”。
晚上做完功课,我开始喜欢去找艾瑞克玩儿。他像一个魔术师,不断地从屋子里翻出值得看的玩意儿。他18岁从家乡格雷迪镇出发,一边给人按摩,一边从事雕塑艺术研究和收藏。在别人眼里他是一个流浪汉,而在他自己心目中,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艺术家。
有一天晚上,我和远在纽约的男友在电话中发生了争吵,情绪不佳的我坐在房间的角落里发呆。艾瑞克走进来,他如孩子般兴奋地拿着他刚编织完工的毛衣在我面前摆pose。这件毛衣是我看着他织成的,图案是中国京剧的脸谱。他知道我喜欢,说是专门给我织的生日礼物。是的,第二天就是我25岁生日了,也是我第一次在异乡过生日,可是男友却忘记了给我寄礼物来,只是在电话中对我说很抱歉。接过艾瑞克的礼物,我忍不住泪流满面。艾瑞克像慈祥的父亲一样抚摸着我的头发,说:“至少他懂得道歉,这正是可贵之处啊。而我非常后悔从前不懂得认错……”
原来艾瑞克结过婚,妻子是一个崇敬艺术崇拜他的农场主的女儿。可是艾瑞克对随着他流浪的妻子并不知珍惜,他那时一心全系在狂热的研究和收藏上。在一个暴风雪之夜,妻子开车给艾瑞克送汽油,不幸掉进山谷摔死了。那时艾瑞克才感觉到心破裂般的疼痛,他对死去的妻子说不尽的歉意和想念。听了他的故事,我的心平静下来,觉得其实男友也是学业太重,我又何必去苛求他呢?
这个晚上,艾瑞克给我看他白天用照相机捕捉下来的街边儿童的笑脸和路边一朵朵无名小花的美态。他取出夏威夷吉他,戴上我送给他的弹古筝用的指甲弹片——他说比他的指甲套更顺手——自弹自唱他几十年前写的情歌。然后,他提醒我说又好久没练琴了。我顺从地打开屋门,坐到琴前,他则和他的猎犬强恩一起偎坐在我的屋门口的地毯上,做两个享受的听众。
这样的时刻,我忘却了生活中的烦恼和繁重的课业,优美的琴声模糊了我们之间年龄、背景、国籍的差别,只剩下两个纯粹的灵魂,在昏暗的灯下因音乐而自在交流、沉醉。
临道晚安前,艾瑞克对我说:“生命太短暂了,我们不能把时间浪费在不快乐上。”我睡在床上,回想艾瑞克说的这句话,再想想和他同住一屋这么久了,真没看见过他有不高兴的时候。哪怕是他半夜醒来写了一首小诗,他也会在清早兴高采烈地读给我听。而那个雷雨交加的下午,当我从考场出来,一眼就看见举着一把用手绘的五星红旗做成的大伞的艾瑞克和他的破车等在路边。原来他在家看见突降大雨,便赶紧做了一把中国伞,很夸张地来接我。这点点滴滴既让我感动,又深深被他“不把时间浪费在不快乐上”的生活态度所感染。
两年学业结束,我被一家声名显赫的大公司聘用,就要离开哈克伦去纽约与男友团聚。临走前的那天晚上,我刚从外面回到家中,推开门一看:天啊!五色的鲜花、五彩的美食、满屋子的中国红五星……这是艾瑞克为我准备的告别宴。坐在桌边,我脑海里已经浮现出他奔波在烈日下,开心地采购、制作的样子。我正不知如何感谢他,他却一本正经地举起酒杯对我说:“非常非常谢谢你!我的中国朋友。”
我有点儿惊讶地看着他。他说:“谢谢你对我的信任肯搬进来住。你知道吗?这对我意义非常重大。”我这才知道,两年前的那个夏天,正是艾瑞克人生中的又一个低谷。他和第二个妻子,一个前外科医生的遗孀,终于结束痛苦的婚姻,而因为精神上所受的折磨,他正在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当时他非常需要帮助别人,他需要来自陌生人的信任,需要为一段友情付出爱,只有这样,他才会觉得快乐和满足,觉得生活依然美妙而精彩。而我这个遥远国度来的女孩给了他信任,给了他帮助我的机会,给了他需要的友情。他发自内心地感激我。他说:“有时候接受别人的爱,也需要勇气。一个不自信、不宽容、不善良的人,是不敢轻易接受的。”
那一刻,泪珠泉水似的从我的眼窝涌出,我说不出一个字,只是紧紧地给了他一个拥抱。很久,我才擦干眼泪说:“我真舍不得离开你……”“傻孩子,”艾瑞克慈爱地看着我说,“爱一朵玫瑰,不能紧紧握住,而是——”他握起一个拳头又摊开来,“要让它成长。你即将开始美好的生活,我很为你高兴。我们有过这么多美好的时光,就够了。”
我一直不明白艾瑞克为什么会对我这样好,我也时常怀着小心眼儿观察他是不是有什么企图。现在,我知道我大错特错了。他其实一直都是在做他自己喜欢的事,他帮助别人是他的需要,他爱别人也是他的需要,并不是为了什么。庆幸的是我当初接受了他的帮助,无意中接受了他硬塞给我的这份关爱,也就在无意中给了他信任。美国人最看重的就是信任,他们认为,你给了他信任就等于给了他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