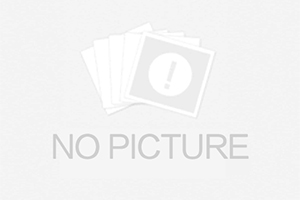1
母亲踅进厨房有好大一会儿了。
我们兄妹几个坐在屋前晒太阳,等着开午饭,一边闲闲地说着话。这是每年的惯例,春节期间,兄妹几个约好了日子,从各自的小家出发,回到母亲身边来拜年。
母亲总是高兴地给我们忙这忙那。这个喜欢吃蔬菜,那个喜欢吃鱼,这个爱吃糯米,那个好辣,母亲都记着。端上来的菜,投了人人的喜好。
临了,母亲还给离家最远的我,备上好多好吃的带上。这个袋子里装芹菜菠菜,那个袋子里装年糕肉丸子。姐姐戏称我每次回家,都是鬼子进村,大扫荡了。
的确有点像。母亲恨不得把她自己也塞到袋子里,让我带回城,好事无巨细地把我照顾好。
2
这次回家,母亲也是高兴的,围在我们身边转半天,看着这个笑,看着那个笑。我们的孩子,一齐叫她外婆,她不知怎么应答才好。摸摸这个的手,抚抚那个的脸。
这是多么灿烂热闹的场景啊,它把一切的困厄苦痛,全都掩藏得不见踪影。母亲的笑,便一直挂在脸上,像窗花贴在窗上。
母亲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我要到地里挑青菜了,却因找一把小锹,屋里屋外乱转了一通,最后在窗台边找到了它。姐姐说,妈老了。
妈真的老了吗?我们顺着姐姐的目光,一齐看过去。母亲在阳光下发愣,母亲说,我要做什么的?哦,挑青菜呢,母亲自言自语。背影看起来,真小啊,小得像一枚褶皱的核桃。
厨房里,动静不像往年大,有些静悄悄。母亲在切芋头,切几刀,停一下,仿佛被什么绊住了思绪。她抬头愣愣看着一处,复又低头切起来。
我跳进厨房要帮忙,母亲慌了,拦住,连连说,快出去,别弄脏你的衣裳。我看看身上,银色外套,银色毛领子,的确是不经脏的。
我继续坐到屋前晒太阳。阳光无限好,仿佛还是昔日的模样,温暖,无忧。却又不同了,因为我们都不是昔日的那一个了,一些现实无法回避:
祖父卧床不起已好些时日,大小便失禁,床前照料之人,只有母亲。大冬天里,母亲双手浸在冰冷的河水里,给祖父洗弄脏的被褥。
姐姐的孩子,好好的突然患了眼疾,视力急剧下降,去医院检查,竟是严重的青光眼。母亲愁得夜不成眠,逢人便问,孩子没了眼睛咋办呢?都快问成祥林嫂了。
弟弟婚姻破裂,一个人形单影只地晃来晃去,母亲当着人面落泪不止,她不知道拿她这个儿子怎么办。
母亲自己,也是多病多难的,贫血,多眩晕。手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疼痛,指头已伸不直了。家里家外,却少不了她那双手的操劳。
3
我再进厨房,钟已敲过十二点了。太阳当头照,我的孩子嚷饿,我去看饭熟了没。母亲竟还在切芋头,旁边的篮子里,晾着洗好的青菜。锅灶却是冷的。母亲昔日的利落,已消失殆尽。
看到我,她恍然惊醒过来,异常歉意地说,乖乖,饿了吧?饭就快好了。
这一说,差点把我的泪说出来。我说,妈,还是我来吧。我麻利地清洗锅盆,炒菜烧汤煮饭,母亲在一边看着,没再阻拦。
回城的时候,我第一次没大包小包地往回带东西,连一片菜叶子也没带。母亲内疚得无以复加,她的脸,贴着我的车窗,反反复复地说,乖乖,让你空着手啊,让你空着手啊。
我背过脸去,我说,妈,城里什么都有的。我怕我的泪,会抑制不住掉下来。
以前我总以为,青山青,绿水长,我的母亲永远是母亲,永远有着饱满的爱,供我们吮吸。
而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母亲犹如一棵老了的树,在不知不觉中,它掉叶了,它光秃秃了,连轻如羽毛的阳光,它也扛不住了。
我的母亲,终于爱到无力。